新闻中心
News

“特朗普只需巧施一策,就能击垮拜登和中国”?|文化纵横
[导读]今日9时(美东时间27日晚9时),美国2024大选首场辩论正式开始,拜登与特朗普再次交锋。这场辩论创下了很多个“第一次”:这是首次在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前举行的总统辩论,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由各自党内推定的两位总统提名人进行的总统辩论。在这场辩论之前,特朗普前国安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再发文,给出了比特朗普在任时更为极端的对华政策意见。他建议,美国应与中国经济脱钩,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增加60%甚至更高的关税,并恢复核武器试验。他认为只有全面削弱中国才能保证世界和平,而这其中的重点就是切断经济纽带。
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之外,奥布莱恩将重点放在了攻击拜登政府“软弱”的外交政策上。他将中国崛起、中东局势动荡、和俄乌冲突都归咎到了拜登身上,认为:(1)这四年来其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模棱两可、自相矛盾,并没有抑制住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发展的势头;(2)拜登政府在中东讨好伊朗疏远沙特阿拉伯,导致了巴以冲突的再度爆发;(3)拜登发表的《如何对抗克里姆林宫》没有丝毫威慑力,撤军阿富汗时美军的表现混乱不堪,奥布莱恩认为,这直接导致了俄乌冲突的爆发。
奥布莱恩的言论一出,便激起了彭博社、英国《独立报》等媒体的批判,而将中国、俄罗斯、伊朗渲染成“反美轴心联盟”的做法更是引发了舆论风暴。我们应当看到,在美国经济承压、社会分裂的情况之下,特朗普为赢得大选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反华立场,意味着未来四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仍不容乐观。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十五,编译自美国《外交事务》2024年7-8月刊,原题为《TheReturnofPeaceThroughStrength:MakingtheCaseforTrump’sForeignPolicy》。小标题为编者自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重振国力,重返和平”
论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实力
罗伯特·C·奥布莱恩
特朗普前国家安全顾问
渡波(编译)|文化纵横新媒体
“Sivispacem,parabellum”是一句四世纪的拉丁谚语,意思是“欲求和平,必先备战”。这一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世纪罗马皇帝哈德良时期,他曾提出“以实力求和平——或者,如果不行,就以威胁求和平”的格言。
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深谙此道。1793年,他告诉国会:“和平是助力我们日益繁荣的最有力工具之一,如果我们渴望获得和平,那么必须让人知道,我们时刻做好了开战准备。”这一理念与罗斯福总统的名言如出一辙:“说话温和,大棒在握。”

而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直接借鉴了哈德良的格言,承诺要“以国力实现和平”,后来他兑现了这一承诺。
2017年,特朗普将这种精神重新带回白宫。在奥巴马任期内,他认为有必要为美国外交政策犯下的“罪行”道歉,并削弱了美国的军备。特朗普上任结束了这种局面。正如2020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宣布的那样,美国“正在履行其作为和平缔造者的使命,但前提是要重振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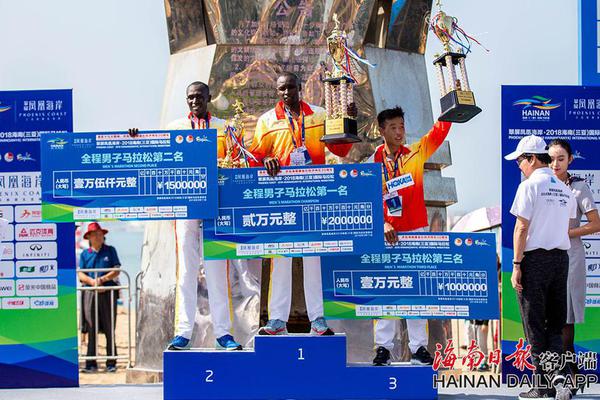
而特朗普确实是一位和平缔造者——尽管这一事实被对他的错误描述所掩盖,但只要看看他的履历,就会一目了然。仅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16个月,美国就促成了《亚伯拉罕协议》,为以色列及其三个中东邻国和苏丹带来了和平;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在美国斡旋下实现了经济正常化;华盛顿成功推动埃及和主要海湾国家解决与卡塔尔的分歧,并结束了对卡塔尔的封锁;美国与塔利班达成协议,在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里,几乎没有美国士兵在阿富汗战斗中丧生。
特朗普决心避免新的战争和无休止的叛乱行动,他是除吉米·卡特以外唯一没有发动新的战争或扩大现有冲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一场罕见的胜利结束了战争,ISIS(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在美军的一场夜间突击行动中被猎杀。
与卡特不同的是,特朗普在和平震慑方面走得更远:俄罗斯没有行动;伊朗没有行动;朝鲜停止了核武器试验;尽管中国没有让步,但他们肯定注意到特朗普对叙利亚进行的“有限但有效的空袭”。
特朗普从未对所谓的“特朗普主义”作出规定,他不遵循教条,而是遵循直觉和传统的美国原则,这些原则比近几十年来全球主义的正统观念更为深刻。“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孤军奋战”是特朗普政府官员经常重复的口头禅,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特朗普知道与其他国家友好合作的重要性。他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交易主义者,或反对联盟的孤立主义者。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北约和美国与日本、以色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军事合作都得到了加强。
特朗普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可以被理解为,是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7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或全球化的负面后果。特朗普及其选民明白,“自由贸易”在实践中并不美好,在许多情况下,外国政府利用高额关税、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盗窃来损害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尽管军费开支巨大,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取得的胜利寥寥无几,而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更遭遇了重大失败。
特朗普对他的前任安德鲁·杰克逊及其外交政策评价很高:在被迫采取行动时要专注且强硬,但要警惕过度扩张。特朗普一旦迎来第二任期,美国将面临杰克逊式现实主义的回归。基于这一原则,华盛顿的盟友将更加安全,更加独立,而华盛顿的敌人将再次害怕美国的力量。美国将重振国力,进而推动和平。
世界现状:下一任美国总统要面对什么?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似乎正处在第二个“美国世纪”的风口浪尖。铁幕落下,东欧国家放弃了共产主义,放弃了华约,排队加入西欧和自由主义世界。苏联在1991年成为历史。中国等少数国家对美国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海湾战争证明了美国在前十年铺垫的军事力量建设是合理的,从而确认了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对比一下当今的情况,中国已成为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对手。中菲涉海冲突、台海局势,可能引发南海更广泛的危机。我们认为,中国是美国网络空间最重要的敌人,其贸易和商业行为更以“不公平的方式”损害了美国经济,这导致美国严重依赖中国的制造业,甚至一些基本药物都要依赖中国。尽管中国当前对第三世界的革命力量和西方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与20世纪中叶的苏联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但中国仍有信心扭转经济。美国应当让中国为新冠大流行负责。
中国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也值得关注。尽管早在2018年拜登就与他人合著了一篇题为《如何对抗克里姆林宫》的文章,但2022年的俄乌冲突表明,俄罗斯丝毫没受到他的强硬言论的威慑。这场冲突还暴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还没准备好应对新的作战环境,即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炮兵等混合作战的模式。
我们应当宣称,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形成一个“反美轴心联盟”。伊朗领导人似乎变得有恃无恐,经常威胁美国及其盟友。根据最权威的估计,伊朗现在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浓缩铀,他们可以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制造出一枚基本的核武器。而在今年4月,伊朗宣布向美国最亲密的中东盟友——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美国家门口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墨西哥,贩毒集团在某些地区组建了平行政府,将人口和非法毒品贩运到美国。委内瑞拉则是一个好战的烂摊子。拜登政府无法确保美国南部边境安全,这或许是其最大、最令人尴尬的失败。
评估中国:未来四年的计划
美国政府软弱无能,深陷泥潭,迫切需要特朗普重振国力恢复和平。在与中国进行的竞赛中,这种需要尤为迫切。
拜登上任以来,他对中国的威胁模棱两可、自相矛盾。尽管他保留了特朗普制定的关税和出口管制政策,但也派内阁官员多次访问北京;在对贸易和安全问题发出严厉警告的同时,也伸出了橄榄枝,承诺恢复特朗普中断的一些对华合作。我认为,拜登的做法是以排场掩盖实质,会议和峰会是活动,并不是外交成就。
与此同时,中国密切关注拜登及其高级顾问的公开言论。尽管拜登将中国经济称为“定时炸弹”,但他也明确表示:“我不想遏制中国”、“我们真的不想伤害中国,如果中国做得好,我们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轻信这类示好就等于轻视了中国这一对手。
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科技发展和创新的领导者,来扩大其话语权及安全范围。在电动汽车、太阳能、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中国政府的巨额补贴构成了“不公平贸易”。拿中国政府扶持的比亚迪等领头电车企业举例,中国为其提供了巨额补贴,并鼓励将数百万辆廉价电动汽车“倾销”到美国和盟国的市场,目的是“让首尔、东京、底特律和巴伐利亚的汽车制造商破产”。
为了在中国的冲击下保持竞争优势,美国必须夺回作为全球投资、创新和经商中心的地位。但美国监管部门日益扩大的权势,包括过于激进的反垄断执法,有可能摧毁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在中国企业从本国政府获得“不公平支持”,“意图挤垮美国企业”之时,美国政府及其欧洲盟友却在拖美国企业的后腿。这是国家衰落的根源,西方政府应该放弃这些不必要的监管。
我认为,美国政府是时候以牙还牙了,就像冷战时期那样。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与中国进行完全的经济分离既不现实,也不可取”;美国“应当放弃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想法”。但事实上,我认为脱钩是可行的,尽管不能明确用言语表达出来。在特朗普任期内,他虽然没有这样说,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约一半产品征收了更高的关税——这是一项事实上的脱钩政策。这项政策本可以促使中国政府以“更正常的贸易行为”与美国合作,然而他们没有抓住机会。现在是进一步施加压力的时候了,正如特朗普所倡导的那样,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并对任何可能对华有用的技术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当然,美国政府应该与中国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但外交重点应当放在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盟友,新加坡等传统伙伴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新兴伙伴上。某些批评人士认为,这些国家会对特朗普要求美国为其提供防御的做法产生担忧。但这些国家官员与我的沟通表明了态度:他们对特朗普的直言不讳表示欢迎,并认为此举可巩固联盟、强化亚洲地区的安全。
所以我认为,与这些国家及地区进行联合军演至关重要。特朗普在2018年取消了邀请中国参加年度环太平洋军演:一个优秀的防御团队不会邀请其对手来观摩计划。美国国会曾在2022年表示,美国应当邀请中国台湾参加军演,但是拜登拒绝了——这项错误的决策可能将在特朗普任期内得到重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对是否向中国台湾提供武器和防御模棱两可。下一届美国政府应当明确作出承诺,并鼓励中国台湾投入更多的军事资金,并扩大兵役制度。
与此同时,美国也应当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提供与以色列类似的赠款、贷款和武器转让支持,菲律宾尤其需要在南海得到支持。海军应该开展一项紧急计划,翻新退役舰艇,捐赠给菲律宾,包括停泊在费城和夏威夷的护卫舰和两栖攻击舰等。
美国海军还应当将一艘航母调往太平洋,五角大楼也应考虑将整个海军陆战队部署到太平洋,以缓解美军在中东和北非的负担。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通常缺乏足够的导弹防御和战斗机保护能力。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国防部应该迅速从其他地方调动资源加以解决。
特朗普的策略:重返极限施压
中东是另一个拜登没能施展实力,进而推动和平的区域。尽管拜登上任后与沙特阿拉伯在所谓人权问题上交恶,但也决定修复与伊朗的关系。这一自相矛盾的做法疏远了沙特阿拉伯,并对驯服伊朗起到了反效果。伊朗在过去四年中变得“更加暴力”,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盟友将这些行动视为美国软弱和不可靠的证据,并采取了更多独立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伊朗感到了“某种自由”,即通过间接的代理人战争或直接战争来打击以色列、美国军队和美国的合作伙伴。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进行了极限施压,包括坚持要求欧洲国家遵守美国和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这种决心得到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美国重要伙伴的支持,并为《亚伯拉罕协议》铺平了道路。当美国盟友看到美国再次下定决心遏制伊朗时,他们将与美国联手,助力对能源市场和全球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的海湾地区实现和平。
不幸的是,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的情况正好相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未能执行。近几个月来,这些出口达到了六年来的最高水平,每天超过150万桶。放松制裁给伊朗政府及其军队带来了巨额财富,每年为他们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而特朗普重启施压将削弱伊朗为“恐怖主义代理部队提供资金”的能力。
拜登的麻烦始于中东,当时他试图重新加入奥巴马时代的伊核协议。2018年,特朗普在意识到这一协议失败后,选择了退出。该协议非但没消除或冻结伊朗的核计划,而是将其合法化。允许伊朗保留离心机,伊朗从而生产了几乎足以制造核弹的铀。特朗普极限施压政策的回归将包括,全面执行美国对伊朗能源部门的制裁,不仅针对伊朗,也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和天然气的政府和组织。极限施压还意味着向中东部署更多海上和航空资产,从而向伊朗和美国盟友发出双重声明: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重点转为威慑伊朗,而不是“镇压”叛乱,就像以往二十年美国做的那样。
特朗普的强硬反伊政策也使巴以冲突得到了有效解决,而在拜登任期内,冲突再次席卷了该地区。几十年来,传统观点认为解决这一争端是改善中东安全的关键。但如今这场冲突已经成为该地区动荡的症状,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伊朗。伊朗政府为一系列威胁以色列安全的组织提供关键资金、武器、情报和战略指导——这不仅包括哈马斯,还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在伊朗被遏制之前,巴以冲突无法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然而该地区的长期治理不应由美国决定,而应当由以色列、埃及和其他海湾地区的盟友协商解决。美国也不应该向以色列施压,迫使他们重返谈判桌,寻求与巴勒斯坦的长期解决方案。美国在中东的政策重点应当是威胁区域安全的“罪魁祸首”伊朗。
拜登的失误:从喀布尔到基辅
拜登在撤出阿富汗时的灾难管理也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外交手腕。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了结束美国参与战争的协议,但特朗普绝不会允许如此混乱和令人尴尬的撤退。人们可以从2021年美军夏季撤军的无能,直接推导出六个月后普京为何决定发起俄乌冲突。在俄罗斯无视拜登警告并发动进攻之后,拜登向泽连斯基提供了离开基辅的手段,这将重演阿富汗前总统加尼的逃离屈辱。幸运的是,泽连斯基拒绝了这一提议。
此后,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但在提供赢得成功所需的武器方面拖拖拉拉。美国国会最近为乌克兰拨款的610亿美元——加上已经批准的1130亿美元——也许能阻止乌克兰战败,但不足以让其获胜。与此同时,拜登似乎没有结束战争的计划。
特朗普则明确表示,他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战争,维护乌克兰的安全。特朗普的做法可能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关键援助,由欧洲国家提供资金,同时为与俄罗斯进行外交谈判敞开大门——并通过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让莫斯科措手不及。他还将推动北约向波兰轮换地面和空军部队,以增强其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军事能力,并明确表示北约将保卫其所有领土免受他国侵略。
美国应该确保其欧洲盟友明白,美国继续保卫欧洲的前提是欧洲也要全力以赴。如果欧洲想表明它认真保卫乌克兰,就应该立即让乌克兰加入欧盟,放弃常规的官僚化入盟程序。此举将向普京发出强烈信号,即西方不会将乌克兰“割让”给俄罗斯。这也将给乌克兰人民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未来会更好。
美军衰败:亟需军队扩容、革新武器及监管采购
当中国崛起、中东战火燃烧、俄乌冲突同时发生,美国军队衰落的势头愈加明显。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一趋势有所缓解。去年,只有海军陆战队和太空部队达到了招募目标,而陆军设定的65000名士兵基数,惊人地出现了10000名新兵指标的缺口。这一缺口反映的不仅是人员问题,还表明了美国年轻人及其家庭对军队的目标和使命缺乏信心。
与此同时,军队越来越缺乏保卫美国及其利益所需的工具。海军目前只有不到300艘舰船,而里根政府末期则有592艘。这不足以维持布局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全球18个海域的海军达到常规威慑。国会和行政部门应该重新致力于特朗普在2017年设定的,到2032年拥有355艘舰艇的海军目标。这个规模略大的海军必须包括更多隐形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增加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潜艇的数量。这是所谓核三位一体的一部分,这些装备和系统可以让华盛顿从空中、陆地和海上部署核武器。
核三位一体的其他部分也需要改进。例如,美国国会必须为正在研发的B-21隐形轰炸机拨款,以替换老化的B-2轰炸机。事实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空军至少需要256架穿透性打击轰炸机,才能对一个同类竞争对手进行可持续作战。为了避免B-2项目中出现的采购问题——该项目最终只为空军提供了21架飞机,而不是最初计划的132架——空军和国会必须共同努力,确保稳定的生产流程。
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核武库总和的技术和数量优势。为此,美国必须对新型核武器进行可靠性和安全性试验,而不仅仅是使用计算机模型。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继续拒绝进行真诚的军控谈判,美国也应该恢复生产铀-235和钚-239,这是核武器的主要裂变同位素。
美国的常规武器库也需要转型。特朗普在任期重启了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而这一项目在2011年由奥巴马大幅削减。这使中国和俄罗斯在获取这种重要的新型武器方面远远领先于美国,这种武器的速度是音速的五倍以上,并且可以在地球大气层内机动。倘若特朗普迎来第二任期,将对这项关键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
恢复军队需要总统和国会领导人的积极参与,因为文职人员和军警人员无法自行修复五角大楼。在五角大楼高级文职官员的官僚主义惰性面前,特朗普能够推动创新。但根本性的改变必须考虑到预算有限的现实。由于不可持续的借贷水平,联邦预算将不得不下降,无论哪一方控制着白宫和国会,大幅增加国防开支都不太可能。在当代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中,明智地花钱将取代花更多钱。
无论是对美军还是盟军,整顿军队都需要对军队的采购流程进行重大改革。近几十年来的一些重要项目,如朱姆沃尔特驱逐舰、濒海战斗舰、F-35战斗机和KC-46加油机,都延误了数年,而且成本远远超过预算。相比之下,在20世纪50年代,洛克希德公司在获得合同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交付了第一架U-2侦察机,并且在预算内完成了该项目。这种成就在今天将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大多数军种的态度都不甚积极,功能失调的国会导致预算和计划均难以实施,军队高层也缺乏远见。
军事采购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五角大楼的不合理制度,导致开发新武器的需求很容易增加,但很难变更。这带来的后果是,武器非常先进,但价格昂贵,而且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投入使用。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设计的航空母舰,包含一个当时尚不存在的技术——即电磁飞机发射系统。就如2017年特朗普的批评所指出的那样,它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和延误。五角大楼的高级文职领导层必须制定一项新规则来改革这一流程,即任何可能增加开发基本系统成本或时间的重大设计变更,必须由他们且仅由他们授权。
美国应该从澳大利亚等盟国的采购系统中汲取灵感。在澳大利亚,精简的官僚机构以低成本开发了GhostBat无人驾驶空中作战车辆和GhostShark无人驾驶水下航行器,而且没有出现美国采购中常见的巨大延误。Anduril和Palantir等植根于创新科技的国防供应商,也可以帮助五角大楼开发更适合21世纪的采购流程。
复兴美国:盟友的重要性
然而,仅靠一支更有效的军队还不足以挫败和威慑中俄伊的“反美轴心联盟”。如果重返白宫,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将继续推进联盟的建立。尽管批评者经常将特朗普描绘成对传统联盟怀有敌意,但实际上,他强化了大多数联盟。特朗普从未取消或推迟过对北约的任何部署。他向北约各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从而使北约更加强大。
相较而言,拜登政府官员喜欢口头上强调联盟的重要性。拜登常常表示,美国及其同盟正在进行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战争。但他又质疑了盟友国家保守派当选领导人的“民主资格”,反倒破坏了联盟。这些领导人包括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波兰总统杜达。事实上,这些领导人响应了人民的愿望,并试图捍卫民主,但他们的政策与喜欢在达沃斯交际的人所信奉的政策不同。然而,拜登似乎对与现实盟友建立良好关系不感兴趣,而更感兴趣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虚构的抽象概念。这种言论反映了一种全球主义和自由精英主义的特质,它伪装成支持民主理想。
有些人可能会说,美国谴责中国和伊朗,但与阿拉伯非民主国家合作,这是虚伪的。但重要的是要考虑各国改变的能力。如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比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更加开放和自由——部分原因是与美国的接触。中国和伊朗却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它们对邻国及地区变得更加危险。
美国并非完美,也并不需要地球上每个国家都与之在政治上相似。纵观美国历史,大多数美国人也认为,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就足够了,而不是将政治制度强加于他人。但美国人不应低估自己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应低估美国在帮助国内外人民摆脱贫困和不安全感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美国如今已经分裂,那么还能复兴吗?尤其是当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走上了错误道路的时候?可正如里根在1980年的选举中所证明的,美国总能扭转局面。今年11月,美国人民将有机会让一位通过重振国力实现和平的总统重返白宫——他可以再次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这样做,这个国家便有了重建国力的资源、才智和勇气,确保自由,并再次成为人类最后的希望。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2024年第22期总第194期




 2024-07-30 17:01:12
2024-07-30 17:01:12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